探索与突破:方案顾问的成长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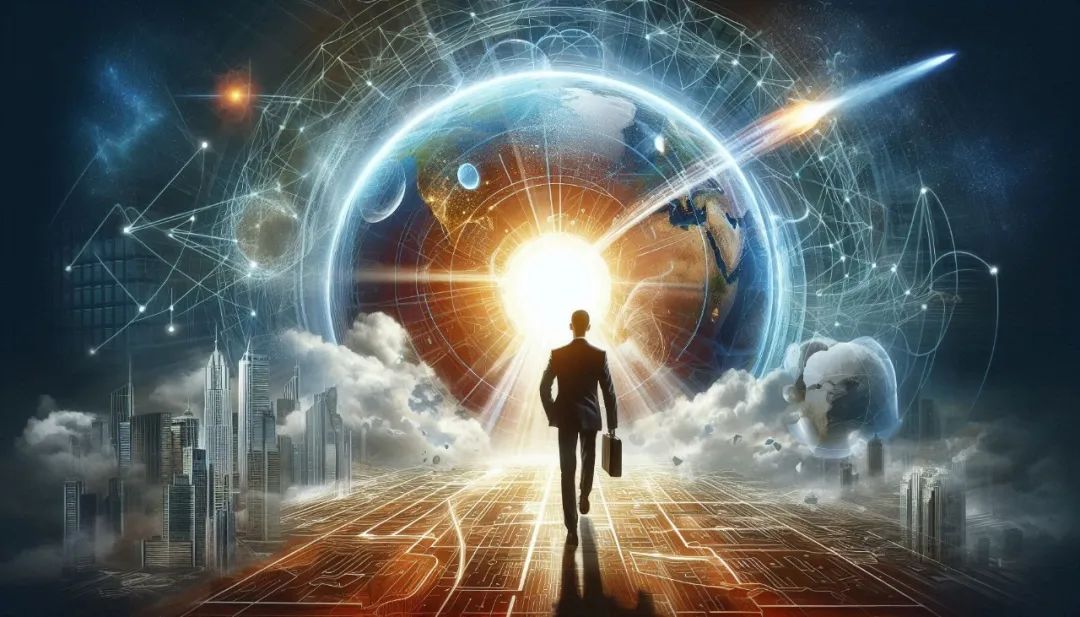

01
起步阶段
我念的是机械专业,做了几年甲方机械设计工程师,因缘际会下1998年转到乙方做CAD工程师。 起初由于是公司里最年轻的员工,被安排去学习刚刚起步的PDM系统(那时也被称为DLM,Digital Lifecycle Management)。 当时,美国总部在项目实施方面只有项目管理的理论方法(PM2),而对PDM系统的实施过程介绍有限,除了一堆功能与开发的说明,没有关于如何进行实施的清晰指导。
几个月后,我被安排去学习数字化制造(那时被称为DM,Digital Manufacturing)。 这次依旧是因为领导觉得年轻人学得快,我在三个月内与客户一起参加外方的培训,在外方离开后,由我一个人来面对客户的四大工艺需求。 某个夏日的午后,我和另一个系统的方案顾问在客户项目办公室讨论两个系统间的接口及相关的用户使用场景。 讨论进行到一段时间,我突然发现项目办公室变得异常安静,转头一看,发现有四五个关键用户正盯着我们看。 我有些惊讶,便问客户是否有什么问题。 他们停顿了一会儿,其中一位关键用户开口说道:“我们突然意识到,两个女人坐在一起讨论了几分钟,就决定了我们企业未来几年的工作方式。 想想这种情况还真有点可怕。 ”这让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作为方案顾问所肩负的责任。

02
初试身手
经过了一年半的四大工艺锤炼后,老板让我开始转型方案顾问SA(Solution Architect)。 我问:“SA要做什么? 我从没做过! ”老板回答:“就像你之前做的那样,把用户需要的功能串联起来,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 好吧,由于在前一个项目中,我开发了很多功能,但自己都不清楚具体在什么场景下该使用哪些功能,于是我尝试画了流程图。 老板看后认为我有潜力,便果断地将我推向了SA的岗位。
我第一次担任SA是在一个整车厂的PLM项目中。 在完成调研后,我对客户的业务依旧感到模糊不清,不得不厚着脸皮请求客户的业务代表帮忙绘制业务流程图。 在得到了业务流程图后,我便开始思考如何将系统功能与这些流程对接。 除了已经熟悉的功能外,我常常查阅线上帮助,有时翻阅到深夜,希望能找到更优化的解决方式。 想方案想到半夜,做梦时也在思考方案场景,突然灵感迸发时,我会在睡梦中急忙醒来,打开电脑将想法记录下来。 压力之大,我曾几次半夜给老板打电话,哭诉自己不知道如何才能让方案系统化,如何才能清晰地表达用例场景,如何确保每个细节都考虑周全。 项目实施过程中,客户还临时要求按照CMII标准检验项目交付物。 经过两年的磕磕绊绊,终于项目顺利完成,交付物也被该客户正式确定为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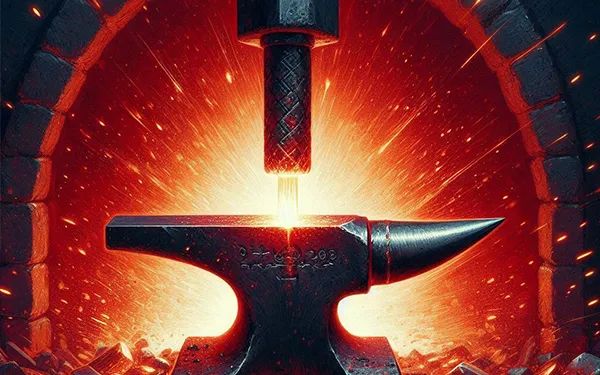
03
锤炼进阶
2006年底,我被借调到深圳参与一个PLM项目。 这个项目号称汇聚了原厂六大办公处的精英资源。 加入时项目已经经历了两个月的调研,我根据调研结论设计了系统实现方案,并与客户进行了讨论。 在交流中,我发现其实有一种更便捷的方式可以实现客户需求。 经过沟通后客户表示,他们希望我们先了解系统如何实现,然后再考虑最合适的业务方案,而不是完全按照他们的想法来进行设计。 这一过程中,我第一次遭遇了思想上的冲突:在项目实施中,是否应该明确区分业务顾问与方案顾问? 业务顾问是否完全不需要考虑系统的实现方式?
2007年,我参与了广州某模具厂的售前项目。 客户要求我们证明实施能力。 应老板要求,我整理了项目实施每个阶段的交付技术文档,并规划了文档章节内容。 这些文档后来成为实施方法论和交付物标准的雏形。 而在实施过程中,客户要求在方案报告中写明必须满足某个需求,但我坚持不同意,因为该需求并不明确,难以清晰表述如何实现。 为此,我与项目经理争执不下,认为方案应明确指出系统如何实现,而不能光写虚无缥缈的内容,给实施顾问和开发顾问埋下不必要的风险。 最终,在老板的仲裁下,项目经理同意说服客户,要求客户在需求明确后再开展进一步讨论。
2008年,我参与了上海的一家电子行业项目。 这个项目进展顺利,客户非常配合,最终实际工时与预估工时之间的差距只有10天。 尽管项目本身很顺利,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客户说的一段话:“你在与我们讨论方案时,总是站在客户公司的角度去看问题,判断怎样对公司最有利。 但有时你忽视了我们各部门的利益。 ”这让我深思:作为方案顾问,设计方案时是否应该始终站在客户公司的整体角度,而不仅仅是迎合某些关键用户的个人需求?

04
攀登高峰
2008年底,我加入了大陆服务团队并开始担任技术经理。 我花了三个月时间重新梳理方法论,同时完善了实施过程中所有交付物模板,作为PLM项目实施的标准规范。 然而,在推进过程中,我遭遇了强烈的反弹,许多人质疑为什么方案顾问需要了解系统功能? 为什么实施顾问必须具备编写开发规格的能力? 为什么要写如此多的交付文档? 这些疑问让我的老板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正巧此时,合肥有一个项目,老板决定让我亲自进入项目,向大家证明我所提出的方法论是行得通的。
于是,我加入了这个备受瞩目的轮胎项目。 项目异常艰难,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轮胎产业兼具离散型和连续性特点,这让习惯于制造业PLM项目实施的顾问在理解业务时遇到了困难,项目最终导致了一名项目经理和一名方案顾问的离职; 第二,客户希望实现全参数化智能设计引导,而公司内部的资深顾问认为这个想法不太现实。 但我认为,客户有清晰的思路并愿意分享他们的知识,这对客户而言是一次创新且富有巨大价值,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在提出这一概念并向客户副总汇报后,以两个月的项目延期为代价,我们最终成功完成了几个设计引导专家系统的实施和交付。
项目的复杂性让一位拥有十多年经验的资深开发人员感叹:“从未遇到过如此复杂的开发逻辑,一个功能竟然需要两天以上才能完全理解其规格。 ”实施过程的艰辛也让客户的一位关键用户在深夜两点多恳求项目组:“拜托,你们休息吧,回酒店去休息吧! ”
在测试阶段,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插曲,用户后悔之前自己坚持的某个实现方式。 我的小徒弟有点幸灾乐祸地说:“谁叫你们当初不听方案顾问的意见,吃亏可就在眼前了。 ”这让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这个项目后续进入二期,并由客户自行负责三期实施。 这个过程证明了作为方案顾问,必须深入了解系统功能,才能确保最终落地的系统与方案保持一致; 实施顾问则需能够编写详细的开发规格,才能让开发人员在不了解业务背景的情况下,能够准确实现方案中定义的功能; 同时,完善的项目交付文档也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确保后续项目执行和运维的顺利进行。
去年,当我再次踏入这家客户公司时,客户说他们认为PLM业务当年已经梳理得非常清楚,除了因已经使用了十几年系统性能稍有变慢之外,其他方面完全没有问题。 听到这番话,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对方案顾问最好的认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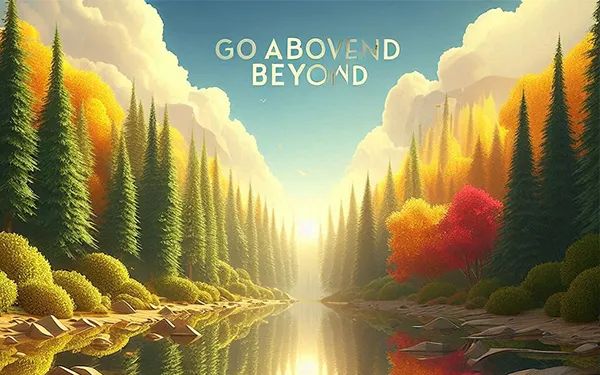
05
超越自我
2014年,我从Teamcenter平台转换到3DExperience平台。
为了争取第一个完全依赖中国本地能力的非外方支持的PLM项目,我再次加入项目组。 通过与项目组资深实施顾问的紧密合作,我逐渐深入了解了系统功能和背后的数据模型。 过程中,一位资深实施顾问显得非常不耐烦,问我:“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些? ”。 我答道:“只有了解系统如何运作,我才能在制定方案时,正确引导客户,确保系统能够支持的功能被充分利用,而不会给实施团队挖坑。 ”这位顾问惊讶地看着我,说道:“从来没有哪个SA像你这样考虑问题,大家通常只是做PPT,然后要求开发出来。 ”于是,另一段披荆斩棘的旅程开始了……
这项目当时该客户已经花大量时间与金钱进行过咨询,也有一整套流程改进的文档。 在项目启动前,客户方项目经理提出了一个挑战,他说我们有完整的流程体系,也特别挑选了你们比较有经验的实施团队,那你们能不能不开展冗长耗时的业务调研而直接开始实施,但又能保障系统对需求的满足呢? 于是,我进行了一个大胆的试验,提出了原型方案设计的实施方法。
除了调整实施方法论之外,这是我第一次担任总方案顾问的角色。 在这个项目中,每个专业领域都有负责的方案顾问(SA)。 作为总方案顾问,我的任务是确保不同领域的方案能够满足业务需求,同时保证这些方案能够无缝衔接并协同工作。
2018年,依托多年原厂实施经验,我开启了自己全新的合作伙伴职业征程……

06
总结归纳
方案顾问确实是一个极具挑战的角色,且方案的优劣常常需要经过多年的使用才能真正显现出来。 一路走来,我十分感激那些包容我的客户和一直为我提供支持的老板。 我始终坚信,作为方案顾问,应该从客户公司长远发展的角度去思考解决方案,方案也必须具备可落地性,避免给实施团队或开发团队挖坑。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我所追求的,始终是问心无愧。
你,期望自己成为怎样的方案顾问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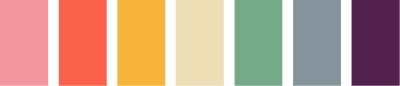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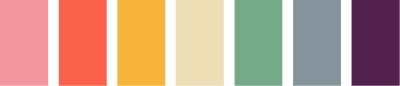
李幼琴
钛闻软件
综合平台技术部联席总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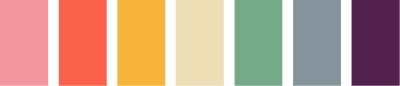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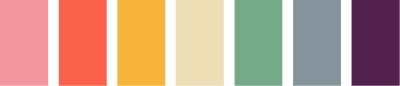
关于钛闻软件

上海钛闻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源自于上海江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2024年1月1日起,钛闻软件全面承接上海江达的人员、业务和相关资质。
钛闻软件在全国设有10个办事处,拥有超过200余人的专家顾问团队和近30年的行业经验,公司致力于向交通运输、工业装备、基础设施、航空航天、高科技电子及生命科学等行业客户提供先进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及企业级应用系统。
作为达索系统重要的合作伙伴,钛闻软件在中国拥有1500多家客户。这些客户长期使用达索系统从需求、设计、工艺、仿真到制造的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总装机量超过30000多套。钛闻软件非常注重客户的实施服务和应用支持,紧扣客户需求,引入最佳实践,让先进软件发挥出相应价值。
